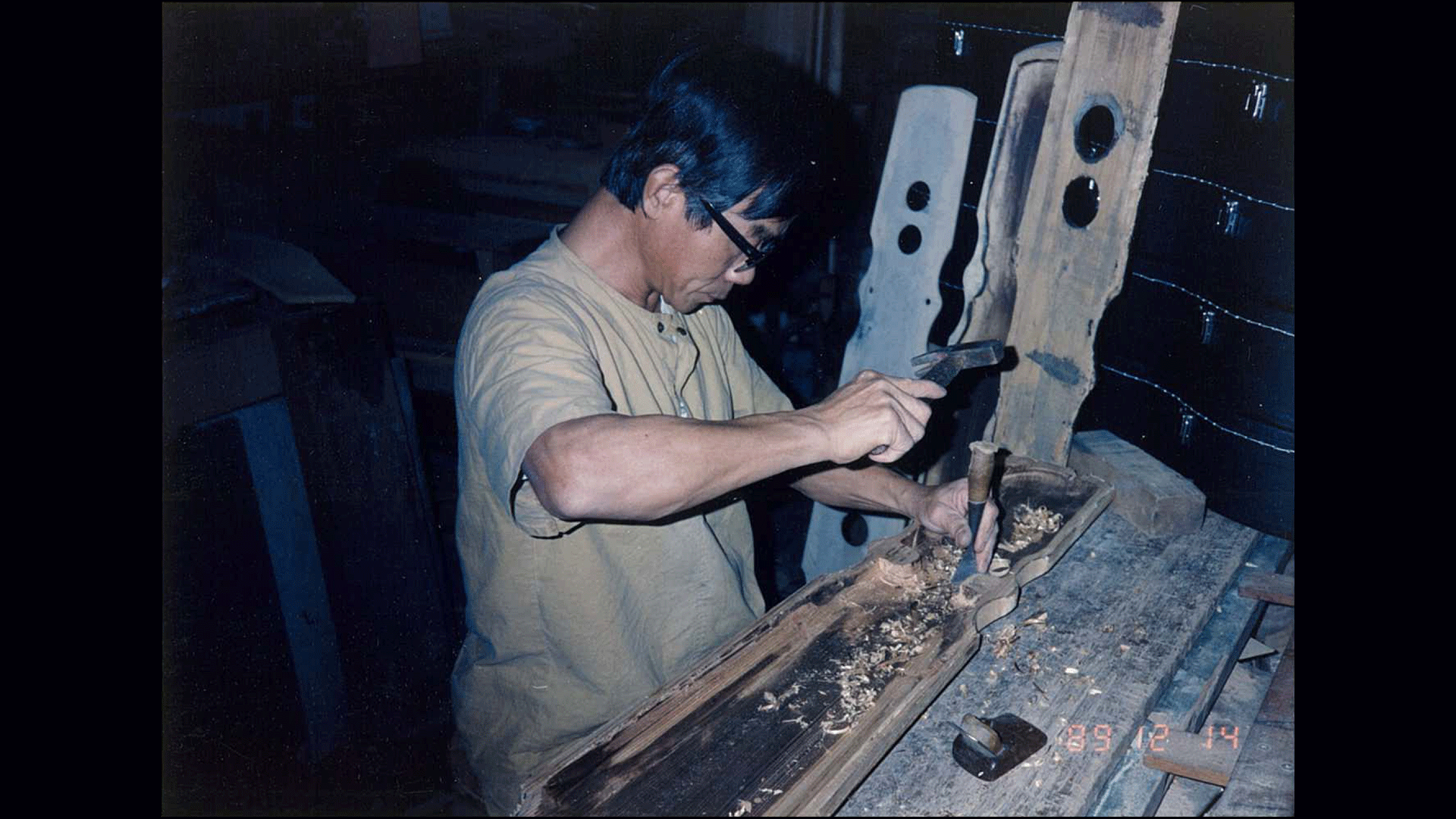千歲文化的二十年傳承週期
關嘉匯
蔡昌壽斲琴學會副會長
香港柳生会總幹事
(原文刊載於《文武之道(下冊)》• 盧敬之等編 • 超媒體出版 )
在《蔡昌壽師傅送給廿二世紀斲琴人的六十課》電影引子裏,我提到古琴的造琴藝術,雅稱「斲琴」,其實是一項一千八百歲的當代藝術。有別於已成過去的古老文化,今日的斲琴於晉代定型後,一直流行至今日,維持了最少一千八百年的「當代」資格。
琴,今俗稱「古琴」,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音樂。「斲琴」是彈琴的人參與樂器創作的文化。有別於一般樂器製作,琴的形態是自由的,件件不同,並背負作者的簽名、命名、題字,是音樂家把美學修為伸延至樂器創作的藝術。
在動盪不安的二十世紀,人類普遍疲於奔命,世界各地不少文化遺產面對失傳的威脅。正當國內琴學於七十年代全面停頓的艱難時期,香港這片福地幸得浙派琴家徐文鏡老師傳授,延續了當時全國最後一脈斲琴。到一九九三年,徐老師的唯一斲琴徒兒蔡昌壽開始收納琴人為徒,二十年間在香港牛頭角及石硤尾的擠迫小工場裏,培育出超過五十位親自斲作琴器的彈琴人,作品張張不同,各具特色。在無人察覺間,斲琴其實成為了香港最具代表性的當代藝術之一。


二十多年間,我們每週末不停打磨、上漆、又打磨,漸漸習以為常成為生活習慣。我深刻感受到自己磨鍊二十年後的一雙手,才剛剛開始觸及蔡師傅那種隨心所欲的技術水平。
環看身邊的人在工餘學習音樂、書法、武術、陶藝,若能持之以恆,技藝亦會在大約二十年後變得輕鬆自如,隨心所欲。我自小研習日本劍術為體育項目,亦同樣於二十年後開始擺脫體力、意念的約束,感到隨心所欲的運作。似乎,二十年是人體學習高難道技藝的一座時間門檻。
三十年前,我在康乃爾大學唸書。因開辦大學劍道部,遇上一位日本柳生劍術世家的高徒,並得他支持,成為尾張柳生家第一個在海外收納的劍術學生。我在大學的全部消遣時間,都浸淫在柳生劍術的研習。柳生家的劍術,家傳超過四百多年至今日。歷代師範的口傳描述,從拆解技術上的微小細節、跨越心理障礙的竅門,到「承」與「傳」的雙向學習系統,有非常詳盡的文字描述,嚴謹地保存給後代師範為鑒。當中,於江戶中期寫下的註釋更是用中文寫的,多年來為我指點迷津。學習、教授劍術的過程讓我深刻明白﹕傳授艱深難學的技藝,必須把自己的心得詳細記錄下來。學生未能體會的道理,只需把答案預先寫下,禁止學生偷看,直到二十年後學生自己成為師範,有了自己的經驗,預先寫下的答案必定能為他解開一些謎團,更極有可能為四百年後的師範排難解困。
在二〇一三年,我構思把蔡昌壽師傅授徒的整個過程拍攝下來,再加以註釋,留給未來的斲琴師範借鑒。計劃獲得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的資助,並於二〇一八年完成拍攝。在斲琴學會多位同學的義務參與下,歷時三年的拍攝花絮被剪輯成紀錄電影《蔡昌壽師傅送給廿二世紀斲琴人的六十課》,向公眾介紹我們的傳承歷程。
記得在拍攝項目的公眾發佈講座中,一位觀眾向我提問。
「為甚麼不用機器,而用人手?」
這位熱心觀眾的意思,是無法理解我們為何在今時今日,仍然以辛苦吃力的晉代古法製作樂器,而不乾脆北上尋找工廠,用五軸CNC與機械噴漆臂進行生產。
「我們也有時用電動工具的,」我笑着回答。「但為甚麼把樂趣讓給機器享受?」
斲琴是創作藝術,就如繪畫,樂趣在自己的雙手之中,不能與印刷品比較。
我跟隨蔡師傅學習斲琴二十多年,接受過多次記者訪問。在在二〇一四年以前,即是在蔡師傅與斲琴學會獲國務院指定為國家級非遺保護單位以前,記者都喜歡以「夕陽工業」的角度進行採訪及描述,未曾有一位記者看穿我們要復興文化的真正動機。
在二戰後的悲慘世界,世界各地急於重建,當代藝術發展由只有二百年歷史的美國主導,以破舊立新、直指人心為賣點。優質的二十世紀當代藝術,會引領我們譁然後深刻思量十五秒,從而換個角度看事物。於是,世界各地的藝術學生虔誠地跑到MOMA參拜被鋸成一片片的母牛軀體,穿上晚裝在音樂廳肅然聆聽長達四分三十三秒的無聲交響樂,譁然十五秒後,回家埋頭構思下一個可能讓世人譁然十五秒的概念。漸漸,「譁然十五秒」成為最保守、最理所當然的當代藝術規條,更成為生活常態。每條轉載、每條廣告,目的都是令你譁然十五秒。博物館內的當代藝術品,早已不比互聯網上的種種譁然更令人譁然,亦不再引起更深層的人性體驗。
今日急速的科技發展,給予年青人十五秒的名成利就機會。年輕人唯有埋頭製作各式各樣令人於十五秒內譁然的事物,才能在巨大企業支配的市場中找到獨立生存的出路。新世代早已不再容許孩子享有一輩子的耐性,賭上一生人的時間,學習一些千錘百鍊的老技術,去抗衡速成即食的新商品、胡剪亂貼的網絡新文化、朝三暮四的生活新態度。
在這麼的一個時代,難怪城市人普遍無法理解延續艱深難學的古老文化的必要性。
傳承千年的古老文化,是今日大行其道的十五秒文化的徹底相反。世上能傳承千年的人類深度文明有一個共通點﹕它必定經歷過數十代師範,每人花盡人生的前一半時間虛心學習、鑽研,再窮盡人生餘下一半時間傾囊傳授給下一代,才達至它爐火純青的水平。當中,這些非遺的「傳」比「承」困難得多,更需要有社會的配合,更需要有可持續的法道。
當世上各種千歲非遺再不能解決從業人的生計,非遺便無法完整地延續其原貌。為吸引學生,不少文化遺產唯有作出變化、簡化、速成化、商品化,讓年輕人學了十堂五課,便能一知半解地自拍十五秒放上互聯網。
這是可悲的現實。但難道世上沒有比自由經濟更合適的方法,讓老文化繼續當代、繼續長青?
一九九三年,是蔡昌壽師傅開始授徒的第一年。我當時在大學唸書,趁暑假,安排行程由美國飛往日本拜候我的劍術老師柳生延春先生,順道跟隨兩位大學教授遊學日本,探索日本古建築,最後回港探親。
一九九三 年是觀摩日本古建築的大好年頭。在京都,木匠正為一千二百歲的東寺進行大規模修葺﹔在三重,二千多位匠人亦正忙着,為伊勢神宮籌備一千三百年來的第六十一次「式年遷宮」。
一九九三 年,日本關西的夏天非常炎熱。當日拜訪京都東寺,工匠帶我們爬上高高搭建在大殿屋簷上的工作室,還未爬到梯頂已全身濕透。我把頭顱探進工作室內,眼前是數以百計的古老工具,整齊地覆蓋着工作室的一整幅木板牆。在互聯網未普及的世界,這些奇形怪狀的鋸、鑿、刨,都是我前所未見的,跟大學木工場的電動工具大不同。我爬進工作室內,回個頭,面前就是數位工匠,正在巨型的斗拱上安裝新的月樑。
「主樑在負重前是造曲的,」教授告訴我們,「但承托屋頂的重量後,主樑會變成完美直線,遇上地震更能橫向卸力,是非常高超的結構科學。」
「這些技法已沿用千年,」一位較年輕的工匠用英語向我們介紹,「於平安時代從中國傳入的。」
唐代至今,日本的古建築經歷過多次的戰亂、地震、火災,也經歷過人民非常貧窮的日子。但這些在中國已寥寥可數的大型木構建築,為何仍能在災禍頻繁的日本,一座又一座屹立着?
我在東寺的屋簷上,忽然明白了。
「這是活生生的當代建築,」我向教授說。

一九九三年東寺•修葺中的屋頂(關嘉匯攝)
日本的匠人在二十世紀吸納了西方的新技術、新文化,卻沒有拋棄故有的老文化。正當世人着迷於奇形怪狀的新建築,謙虛沉實的老工匠卻自得其樂地延續東方木構建築,與在旁的大自然完美結合。
我們的康乃爾大學考察隊在京都、奈良一帶住了一個月後,乘搭火車到三重,參觀快將進行「式年遷宮」的伊勢神宮。伊勢神宮的神社羣組,相傳起源於一千五百至二千年前。當中,以供奉天照大御神的「內宮」及供奉豐受大御神的「外宮」為首,被譽為全日本最崇高的聖地。伊勢神宮的建築模式並非於唐代傳入的中國木構建築,而是日本本土的古建築。我心情興奮,非常期盼也能爬進匠人的工作室,細看神宮的修建。

一九九三年東寺•木匠的弧度尺(關嘉匯攝)

一九九三年伊勢神宮•外宮參道(關嘉匯攝)
路上,兩位教授沒有說話,直到我們抵達神宮的參拜石路。
「左邊圍牆後面,」教授指向左邊的圍牆,「是現在的正宮,快將拆掉。右邊圍牆的帳篷後面,是未來二十年的正宮,差不多建好了。」
我們步近正宮圍牆。門口被繩索、布簾攔住。
「風起的時候,」站在老遠的教授提起嗓子叫道,「布簾會被吹起,拚命望吧,就只有那個時候能望進裏面。」
風起,布簾飄揚,我探頭望進去,見一片長方型的石地,後面再有一幅圍牆、一所門樓;我伸長脖子,還是看不見後面的正宮,布簾已垂下來。
「正宮在第三層圍牆後面,」教授叫道。「外宮與內宮大致一樣,也不准內進的!」
一位來自波多黎各的同學高聲驚呼。「我們搭了半天火車,就是來看這條布簾?!」
「過往一千三百年,人們都是步行來的!」教授回答。「我們搭車,真欠誠意!」
伊勢神宮跟世上所有古建築物都不同。第一,它既是古建築、也是當代建築。自一千三百年前,每隔二十年,伊勢神宮的六十五座木造建築物會被解體拆卸、再以全新的材料按照原貌重新建造一次。舊宮拆出來的樑柱、器物會被運往全國各地,用

一九九三年伊勢神宮外宮 • 正宮門前布簾隨風飄揚一刻(關嘉匯攝)
於其他神社的興建、維修。第二,建築物的所在地址,都分為左右幅地,一幅是上一個二十年的,一幅是下一個二十年的,輪流交替。今年拆左建右,二十年後拆右建左。整個重建過程需時八年,稱為「式年遷宮」,當中包含植樹、耕作、捕魚、煮食、編織、採材、製物、運輸、建造。新一代的二千位頂級工匠,有二十年時間追上上一代二千位工匠的技藝,而上一代工匠亦有二十年時間,為新一代工匠提供參考、核實,直到二十年後,傳承週期大成。
另一位女同學苦笑叫嚷,「教授忘了寫信申請入場嗎?!」
「這是神的地方,」教授回答。「妳要入場幹甚麼?」
原來,日本最崇高的聖地不是一棟甚麼遊客打卡熱點。伊勢神宮是二千個二十年傳承週期、二千個傳統活化、二千個標準覆核。每二十年一次,它的成果會被分享至全國各地,成為當地的榜樣、模範。伊勢神宮守護的,是人類對文化傳承的尊重、承擔、堅持。參與者以外的人,當然只准在外窺探,不得入場騷擾。
人成長後,有大約四十年最活躍的時間,足夠以二十年實踐「承」,再以二十實踐「傳」,直至技藝達至爐火純青。深度文化就是這樣延續至下一代。
人類經歷了悲慘的二十世紀,由戰亂、貧窮中走出來,忽然進入了今日的科技爆炸時代。為糊口,我們別無選擇地疲於奔命,不停追趕新科技,設計新產品,創作新服務,吸引新顧客,滿足新要求。幸運的產物在十五年後落伍﹔較多產品在十五個月內被淘汰﹔最多產物在十五秒內被人忘卻。為競爭,生產線越搬越遠,機械人取代人手。越先進的國家,人就越失去用雙手進行實體作業的機會。但人類經歷了百萬年的耕作漁獵,用兩手作業的樂趣卻是人性的重要部分。於是,今日城市人的工餘文化包羅萬有,正是為了滿足人性對親手植樹、耕作、捕魚、煮食、編織、採材、製物、運輸、建造的本能渴求,平衡枯燥乏味的幹活。技藝早已不再是為生產而存在,而是為人性而延續。
在這個新世界,擁有深度文化的社會,才能讓近者悅,遠者來。失去文化,社會就失去自身的凝聚力、吸引力。
現在,正是中國文化復興的大時機。我們把握好這個時機,就能把險於二十世紀失掉的古文化、老智慧活生生地延續,納入日常生活,成為當代文化。但把握不當,老文化自行以商業化的模式延續下去,為着取悅更多耐性有限的新學生,必然會出現簡化、商品化、速成化的趨勢,從而變質,最後喪失其深厚內涵,變成孩子與孩子之間的競技。單靠自由經濟,老文化今日再不能自行完成傳承週期﹔我們需要國家政策提供框
架、目標、時間、地點,集合捐獻,融合力量,計劃長遠的文化傳承週期,才能把千歲文化原汁原味地延續千歲,分享給所有人。這就是伊勢神宮的智慧,值得我們中國人虛心學習。而伊勢神宮的經驗告訴我們,二十年就是文化傳承週期的基數。
我自中學在北美居住,大半個童年很少機會用中文說話。只因小時讀過一本有關孔子的漫畫書,知道孔子是古琴高手,我自幼對琴着迷。終於,我在八十年代末買到一張由一所上海樂器工廠製作的仲尼式琴,品質非常欠佳,但至少有它陪伴我在北美生活,作為我僅餘的中國文化。在那個時代,全球彈琴的人非常少,我亦找不到居住在北美的導師,唯有拿那個琴,胡亂彈奏任何自己會哼的曲子。那就是青年的我。
一九九三年夏天,我完成日本古建築考察之旅後回港探親。就在返回美國開學前的星期天,跑上中環三聯書局選購中文書。我在那裏巧遇蔡昌壽師傅唯一一次的個人琴作展覽,震撼難以言諭。我把蔡師傅的卡片保存在錢包內,直到一九九七年回流香港,第一時間拜蔡師傅為師,研習斲琴作為自己每個週末的消遣。我就這樣,展開了兩個二十年傳承週期;今日還在不斷尋找方法,把斲琴與劍術帶給我的無窮樂趣,延續給下世代。
二〇二〇年九月